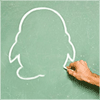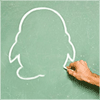
用户8420497703481
公元前129年,馆陶公主府上来了一个卖珠宝的妇人,丧夫不久的刘嫖对妇人13岁的儿子来了兴趣。她连连赞道:“这男孩儿长得真标致!”于是牵着男孩儿的手说:“我替你母亲抚养你,如何?”
妇人僵在原地,指尖攥着锦盒的边角泛白。她望着眼前金钗环绕的馆陶公主,又看看儿子懵懂仰头的侧脸——那孩子还不知道,这句看似温和的问话,会把他拖进怎样一张权力织就的网里。最终,她屈身叩首,锦盒“咚”地磕在青砖上,发出细碎的响声。
男孩儿名叫董偃,从那天起住进了公主府的偏院。刘嫖请了先生教他读书击剑,甚至亲自指点他如何应对王公贵族。这孩子像是块被精心打磨的暖玉,不多时便学会了察言观色,递茶时手指的弧度都恰到好处,笑起来眼角的细纹能熨帖地融进宫里的规矩。府里的老仆私下议论,说董偃看公主的眼神,早没了初见时的怯生生,倒像是藤蔓缠上了老树,分不清是依赖还是攀附。
十三岁的少年总爱溜到后院的梨树下打盹。有回刘嫖寻过来,竟摘下钗子替他拂去肩头的花瓣。阳光穿过花隙落在她鬓角的银丝上,董偃忽然想起母亲临别时红着的眼眶。他猛地坐直,刘嫖却按住他的肩:“怕什么?在我这儿,你想怎样就怎样。”可他分明看见,她袖口的暗纹里,藏着和未央宫地砖一样的冰冷图案。
几年后董偃长成了翩翩公子,成了公主府里公开的“主人翁”。长安城里的权贵都知道,要想见馆陶公主,先得经过董偃这关。他陪刘嫖掷骰子到深夜,赢了便歪在她膝头撒娇,输了就耍赖要她腕上的玉镯。没人觉得不妥,连汉武帝见了,都笑着喊他“主人翁”。
可梨树下的盹,渐渐睡不着了。有回董仲舒路过,冷冷丢下一句“私侍公主,秽乱男女”,董偃吓得摔了手里的酒盏。他开始躲着刘嫖,在书房里一遍遍地临摹《论语》,可笔尖总抖得厉害。刘嫖看出他的不安,竟带着他去见汉武帝,半开玩笑地说:“这孩子怕您治他的罪呢。”汉武帝大笑,赏了他黄金百斤,可那笑声落在董偃耳里,比董仲舒的斥责更让人发寒。
二十岁那年,董偃病了。起初只是咳嗽,后来竟咳出血来。刘嫖守在床边,亲手给他喂药,鬓边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。董偃望着帐顶绣的鸾鸟,忽然轻声说:“我想回当初那个巷子里,看我娘卖珠子。”刘嫖的手顿了顿,把药碗重重放在案上:“这里不好吗?有穿不尽的绫罗,吃不完的珍馐。”他没再说话,只是闭上眼,眼角滑下一滴泪。
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岁。刘嫖不顾朝臣非议,执意把他葬在自己的陵园旁,两座坟冢隔着一条小路,远远望去像是依偎在一起。长安的百姓路过,总会指指点点,说那少年郎享了十年的荣华,终究是成了馆陶公主墓碑上一道模糊的刻痕。
没人记得,那个13岁的孩子被牵进公主府时,手里还攥着半块母亲给的麦芽糖。更没人知道,他临终前攥着的那卷《论语》,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梨花。权力场里的情爱,从来都带着算计的甜,可甜到尽头,只剩噬骨的凉。
参考书籍:《史记·佞幸列传》、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